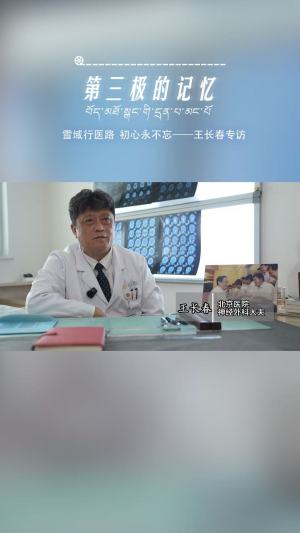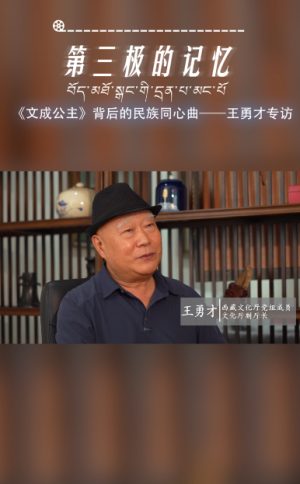作为土生土长的那曲人,童年记忆中最深刻的家乡场景是什么? 作为首批“内地西藏班”学生(1988年), 谈谈您当时离开高原到内地求学的感受?
让我感到记忆深刻的上学场景是住简陋的土房教室,两个人共用一张木桌,围坐在火炉旁,和同桌共用一支铅笔。
我是1988年赴天津红光中学学习第4批的学生,当时最大的想法是:哇!可以坐飞机了,飞向蓝天,就像雄鹰一样。我想这应该是个人成长与求知的一种渴望吧!“内地西藏班”的政策鼓励我们藏族学生到内地学习,不仅提供了稳定的求学机会,还在生活、学业等方面给予保障,让家长和学生有了坚实的后盾。
80年代的西藏,教育资源相对有限,内地在教学条件、师资力量、课程设置等方面更具优势。对于渴望学习知识、开阔眼界的藏族青少年来说,内地提供了更广阔的成长平台,能接触到更丰富的文化和先进的理念。当时我们怀揣着“学成归来建设家乡”的想法。我想这既承载着个人的理想,也寄托着家乡和国家的期望。
谈谈您在内地的这段求学经历,这对您作出“回到西藏教书”的选择有影响吗?
内地的教学资源更丰富,课程体系更完善,不仅接触到扎实的学科知识,还能通过图书馆、实验室、课外活动等,了解到更前沿的科技文化和思想。这种视野的打开,让我跳出了原来相对局限的认知。在内地学习的七年时间里,我深刻感受到国家对西藏发展的重视。这种体验让我更加明确:个人的成长始终与家乡的命运紧密相连。内地教育给了我“走出去”看世界的机会,而这份积累,更应该用在“回来”建设家乡上——带着学到的知识、开阔的视野,为西藏的发展添一份力,这种选择让我觉得更有意义,也更能体现自身的价值。
可以说,内地的经历让我既看到了外面的世界,也更看清了自己与家乡的联结,回到西藏,是自然而然的选择,也是内心深处对这片土地的责任与热爱。
您认为内地培养模式为西藏教育带来的改变是什么?
第一,打破了西藏本地教育资源相对有限的局限,为藏族学生提供了接触更优质教育资源的机会。内地完善的课程体系、弥补了西藏在教学上的短板;第二,为西藏培养了一批具备扎实知识储备和开阔视野的人才。通过内地学习,不仅提升了学业水平,还积累了跨文化交流、自主学习等能力,成为西藏教育的发展储备力量;第三,内地西藏班的办学模式,将内地先进的教育理念、教学方法(如素质教育、互动式教学等)引入西藏教育的视野。大量内地西藏班的学生毕业后回到西藏,很多人投身教育行业,他们将在内地学到的知识和经验用于西藏的教学实践中,成为连接两地教育的纽带,直接为西藏教育质量的提升贡献力量。
“内地西藏班”学生的成长经历也激励了更多西藏家庭重视教育,让“通过学习改变命运、建设家乡”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,间接推动了西藏整体教育氛围的改善。
那曲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,您认为在高寒缺氧环境中开展教学,面临的挑战是什么?
高寒缺氧会导致很多的身体问题,长期处于这种环境中,师生的体力和精力容易透支,直接影响课堂专注度和教学效率。尤其是低海拔地区援藏的教师,汉族教师需要较长时间适应,还有和孩子们语言上沟通的困难。汉族老师在与学生接触过程中,都在努力学习藏语,大多数老师能简单地与家长学生进行沟通,甚至还有很多老师,也能流利地说出一口本地藏语。我觉得这一切都来自于他们的用心、认真与责任感。作为同事,我非常佩服他们,也觉得非常值得我们学习,作为那曲本地人,我从内心深处感谢与感恩他们。
还有就是教材与教学内容适配性,部分内地编写的教材内容可能与高海拔地区的生活实际、自然环境关联度较低,需要教师额外调整教学内容,才能让学生更好地理解。
在基础设施有限的年代(如早期无暖气、停电),如何保证课堂质量?
我们早期参加工作那会儿,教育的基础设施是非常有限的,但我们不会因为基础设施的一些缺陷去减短或者缩小上课的时间。那时候,课堂质量靠的不是一些先进的教学设备,而是师生对学习时间的珍视。很重要的一点是,教师以身作则:面对困难,教师很少抱怨,而是用积极的态度感染学生。学校开展劳动课,组织学生一起去捡牛粪,每间教室安个火炉,烧牛粪取暖。晚读或阴天停电时,点燃蜡烛(虽光线昏暗,但全班围绕灯光集中就坐,反而拉近师生距离),教师放下对条件的依赖,回归教学本质;学生在艰苦中更明白学习的意义,这种双向的投入,在有限的条件下,依然能实现知识的传递与吸收。
您多次获得语文教学奖项,在藏区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中,遇到过哪些难题?如何让孩子们爱上汉语诗词?
藏区部分偏远农牧区长期以藏语为主要交流工具,家庭、社区的日常沟通几乎全用方言或藏语,学生缺乏使用国家通用语言的“沉浸式场景”。例如,孩子在学校刚学会的普通话词汇,回到家后因家长听不懂、用不上,很快就会遗忘,形成“课堂学、课后丢”的循环。低年级学生对抽象的汉字、拼音理解困难。对汉语的语序、语法规则(如“把”字句、“被”字句)难以适应,初期学习时容易产生挫败感。我们在教学的过程中,把诗词变成“可触摸的游戏”,教《静夜思》时,让孩子们画一画自己家乡的月亮;学《春晓》时,去校园里找发芽的小草、唱歌的小鸟。让抽象的文字变成听觉、视觉、动觉的体验。
您曾获“师德标兵”,在您心中,高原教师的“师德”核心是什么?
在我心中,高原教师的“师”之核心,是“把根扎进高原,要把心交给学生”。作为老师,首先得有“耐得住”的坚守——耐得住高寒缺氧的艰苦,耐得住远离繁华的寂寞,把自己当成高原的一分子,不是“过客”。 更重要的是“捧得出”的真心。
高原的孩子可能不善表达,但特别重感情。你是不是真的为他们好,核心不是“我要教他们多少知识”,而是“我要让他们相信,自己能走出高原看世界,也能带着本领回来建设家乡”。这种信念,比任何教案都有力量。坚定理想信念,有爱国情怀,要求老师自身要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,这不是一堂课,也不是一句话,需要润物细无声。
在您教书育人的过程中,面对部分家长“读书不如放牧”的观念,您如何走进家庭,说服家长?
与其说是“说服”,不如说是“一起慢慢看见读书的意义”。宣传党的好政策,比如说是5年的免费教育,“三包政策”,孩子们营养的改善,使农牧民学生上学无负担等措施。家长们大多淳朴实在,其实家长不是反对读书,只是怕“读书没用”。他们的想法往往源于生活经验——比如自己靠放牧、务农也能养家,觉得“看得见的手艺”比“看不见的书本”更可靠。通过读书改变生活的孩子,比如考上师范回来当老师的年轻人,包括我们自己的亲身经历,用“咱认识的人”的真实经历,代替空洞的“读书有用”。家长心里都装着孩子,只要让他们看到读书能给孩子铺一条更宽的路,这条路既能通向远方,也能扎根家乡,他们总会慢慢和我们一起推着孩子往前走。
您说“为育人而教书”,在语文课堂中如何培养“正直的社会建设者”?
在每一次文本细读的思考与表达中挖掘“正直”的基因。
比如学习五年级下册课文方志敏《清贫》后,我利用午间阅读课,和同学们一起共读了方志敏同志的另外一篇文章《可爱的中国》节选。其中有这样一句:“欢歌代替了悲叹,笑脸代替了哭脸,富裕代替了贫穷,健康代替了疾病,智慧代替了愚昧,友爱代替了仇恨,生之快乐代替了死之忧伤。”有学生将其抄下来,并在阅读笔记上写下感想:只要我们努力学习,去完成我们的中国梦,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方志敏……还有一段佳句:“无论如何,我们决不能让伟大的可爱的中国,灭亡于帝国主义的肮脏的手里。”学生的感想:虽然这篇文章是在暗黑的囚室里写的,可他(方志敏)的内心是光明的,因为他是那么忠诚于国家,爱国心就像一束光照耀着他,我要向他学习。”“方志敏叔叔,你所向往的美好中国,正在渐渐实现,我们一定努力学习,使我们的国家变得更好”。
通过阅读课,阅读英雄故事,让孩子们体会英雄人物形象,用文字表达感想,让学生明白,我们应该珍惜现在的生活,也让学生明白,我们要有爱国情怀,要懂得感恩。
在语言实践中践行“正直”。比如六年级下册“学写倡议书”,以倡议书的形式,让孩子们发现身边浪费粮食的现象,“你认为应该怎样去做?说出你的观点”。让写作成为自我反省的载体,让表达成为价值观的镜子。这也是在践行一种朴素的正直—对劳动的尊重,对资源的敬畏,对他人的体恤。当学生能从文字中看见人性的光辉,在表达中坚守内心的尺度,语文课堂便真正实现了“教书”与“育人”的同频。
您如何看待“援藏教师”与“本土教师”的互补性?
援藏教师带来内地先进的教学方法(比如多媒体教学、小组合作模式),通过他们的牵线,可能为学校争取到图书、教具,甚至和内地学校“结对子”,让孩子有机会和远方的同龄人通信,这种“连接”本身,就拓宽了教育的边界。本土教师是最懂这片土地和孩子的人。援藏教师可能轮换,但本土教师是“坚守者”,能在漫长的教育过程中,持续关注孩子们的成长,这种“细水长流”的陪伴,是教育最需要的。
我还听过这样一句话:援藏教师带来的“新”和本土教师坚守的“土”,前者让孩子知道“山外有山”,后者让孩子明白“脚下有根”。说到底,无论是“援藏”还是“本土”,大家的终点都是一样的:让孩子有选择的权利,有幸福的能力。这种目标一致下的互相成全,就是互补性最珍贵的地方。
您如何将内地所学转化为适合高原孩子的教学方法?
在写作课上,我们将一些较为抽象的内容变成我们身边能看得见、感受到的事物,这样孩子们学起来更快。
我们五年级课本有个说明文的写作课,介绍白鹭。我们把“白鹭”改成“牦牛”,以当地举办的畜牧业为平台,向游客们介绍家乡牦牛,介绍牦牛在牧区生活当中的重要性,,以及到了冬宰,卖出去一头牛的收入是多少,以列数字、作比较等说明方法介绍家乡的牦牛。我们生活当中对牦牛非常熟悉。孩子们也许不懂得,但是以调查的形式让学生回家去做,与家人进行沟通,家里的爷爷和爸爸在这方面是高手。
从1980年代至今,您亲历了西藏教育哪些重大变革?
从普及六年制小学教育(扫盲) 到将九年义务教育法定化。从“有学上”到“上得起学”,西藏实现义务教育阶段“三包”政策(包吃、包住、包学习费用),后来扩展到高中阶段,彻底打消农牧民“供不起孩子上学”的顾虑。
1985年首创的“内地西藏班”,在这一时期扩大规模,从最初的几所学校增至全国20多个省市的百所学校。越来越多高原孩子有机会到内地接受教育,带回新视野,我就是受益于这一政策的学生之一。“互联网+教育”让偏远学校也能连上优质资源——通过直播,我们的师生可以听名师讲课,电子白板、在线题库进入课堂,改变了过去“一支粉笔、一本书”的教学模式。
如今走在西藏的乡村,最漂亮的、最新的建筑往往是学校,“十年树木,百年树人”“为党育人,为国育才”大字非常醒目。
您理想中的“扎根西藏的建设者”需要具备哪些特质?您的学生中是否有让您欣慰的传承案例?
愿意与这片土地“共生”的人,甘于平凡的人。我有很多学生都从事着教育工作,大部分都在县城和乡村担任老师,他们都是平凡的教育工作者。教师在三尺讲台上,用一支粉笔、一块黑板,挥写着自己的青春年华。当我们的学生从四面八方捷报频传的时候,我感觉我们的路同样辉煌。我们不是“太阳”,不能与“太阳”去媲美,但我们愿意把阳光折射给学生,只要他们灿烂,我们就是满足的。
如果让您再次选择,您是否仍会选择回到那曲,做一名小学教师?
我仍然会义无反顾地选择回到这里当一名小学教师。这里是生我养我的土地,我深爱着这片土地。最初我背上行囊,离开家乡去内地西藏班求学,我们的初心就是学成归来建设家乡。我觉得小学的教师教育事业是一种“叶”的事业。诗人泰戈尔说过:果子的事业是尊贵的,花的事业是甜美的,但是让我们做叶的事业吧!叶总是谦逊地、专心地垂着绿荫,每一位小学教师都像一片绿叶。
您希望人们在《第三极的记忆》中记住什么?
记住西藏在党的优良政策下不断发展、蒸蒸日上的教育事业。记住默默坚守初心,用“绿叶”的事业在党的阳光下,每时每刻进行着光合作用,孕育着花和果,孕育着这片土地上的万千桃李的平凡的人民教师。